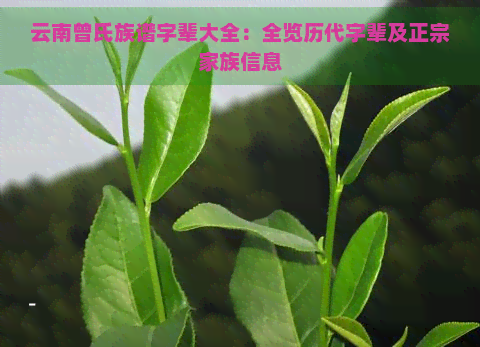作者:让-米歇尔·傅东
译者:易二三
校对:覃天
来源:Sabzian (2025年4月30日)
在《在异国》(2012)中,伊莎贝尔·于佩尔与洪常秀在韩国日复一日地精心塑造角色,而在《克莱尔的相机》(2017)中,她又在戛纳如梦似幻的氛围中完成拍摄。
如今,两人再度合作,共同打造了新作《旅行者的需求》,该片在2024年柏林电影节上斩获银熊奖。去年3月在巴黎,就在《旅行者的需求》斩获大奖不久后,于佩尔回顾了她与洪常秀的合作——他将即兴发挥与精准掌控相结合的创作方式——以及她对表演的理解,她对「活生生的切入点」的追求。
《旅行者的需求》
这是洪常秀的第32部电影,也是他与于佩尔合作的第三部作品,后者在片中饰演独自在首尔生活的法国女性伊丽丝,有些迷茫,靠教授语言课程谋生。伊丽丝身着一件绿色开衫和一条短裙,她的外貌与她的处境一样独特——她为何来到韩国的原因仍不明确——在首尔的街道和公园中,与她的学生或路人展开了一系列邂逅。
这些时刻逐渐揭示出一种既令人不安又令人发笑的怪异感,这种神秘因其轻盈而更加深邃,在醉酒的对话或慵懒的调情中浮现。可以说,《旅行者的需求》凝结了洪常秀电影中标志性的令人惊叹的诗意能量。
让-米歇尔·傅东
傅东:《旅行者的需求》是你与洪常秀合作的第三部电影。你还记得你们是怎么相识的吗?
于佩尔:当然,我记得非常清楚。2010年在巴黎MK2 图书馆影院的大厅里,当时他和克莱尔·德尼待在一起,他们俩关系很密切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
后来,我去了首尔参加「女性肖像」展览,该展览当时正在全球巡回展出。我想到邀请他来参加开幕式,他应约来了。他提议我们再见一面;第二天,我们一起吃午餐,他带我去了一个奇怪的地方,天花板上都是汽车的车顶。我问他接下来打算做什么,他告诉我正准备拍摄一部新片,但对剧情毫无头绪。
他唯一确定的是拍摄地点——一个他钟爱的海边小镇莫汉里(Mohang-ri)的一家小型海景酒店。这正是他创作方式的典型特征:大多数导演会从主题或剧情构思入手,而他仅凭对某地的喜爱就能构建一整部影片。
傅东:你对他的电影很熟吗?
于佩尔:其实不太了解,我是在1998年偶然看了《江原道之力》后,才开始关注他的作品。我并没有逐部追踪他的所有作品,但我知道自己深深喜爱他所代表的电影理念。因此,在那次午餐时,他突然问我是否愿意出演他的电影——当时连故事的雏形都没有——我还是答应了。就这样定了。
我回到巴黎后,我们远程确定了拍摄日期:七月初的十五天。随后,他通过邮件寄给我即将被分为三幕的《在异国》的前两幕的剧本。
《江原道之力》
傅东:你有问他什么问题吗?
于佩尔:是的,尤其是关于服装的问题。他让我给他发一些我拥有的衣服的照片,但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复,所以最后我带了一大堆不同的服装,好几个行李箱,前往韩国。他还问我是否愿意独自前往,这其实正合我意。他告诉我,等我到了之后,他会介绍我认识一位化妆师和一位发型师。
我抵达韩国时,他亲自来机场接我——这通常不会发生,导演们通常不会来接我——而且他身边还带着韩国的影星刘俊相。这与大多数电影拍摄的方式大不相同,但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安排。
傅东:在那个时候,有剧本的雏形了吗?洪常秀的电影总是给人一种即兴创作的强烈感觉。
于佩尔:哦,完全不是!一切都写得非常精准。只不过我在开拍时才收到剧本,大概每天会有一天时间准备。
傅东:你刚才提到他还给你介绍了化妆师和发型师……
于佩尔:洪常秀带我去了美发沙龙,那里的一位美容师为我化妆,一位发型师为我理发。他问我感觉如何,我说我觉得很完美。他然后说:「好吧,我们就用她们吧。」结果她们全程陪同了整个拍摄过程。后来我才意识到,她们并不是电影行业专业人士,而是那家美发沙龙的员工。她们其实并不认识洪常秀。但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。
傅东:然后呢?
于佩尔:我把自带的所有衣服都给他看了,他就像画家挑选颜料、调配调色板一样。他注意到一件我前一年在菲律宾拍摄布里兰特·曼多萨的《人质》(2012)时,在超市买的蓝色衬衫。我并不特别喜欢那件衬衫,但他认为它正是这个角色在第一幕所需的完美单品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从拉斯维加斯买的一件橙色连衣裙和一件Zara的连衣裙上。他从中看到了色彩的搭配、色彩的语言、美感和幽默感。
然后我们开车出发,抵达了一家小而简朴的酒店。第二天,我们开始拍摄。他给我讲了第一场戏的全部台词,我们就直接开拍了。我们原计划拍摄十二天,但九天后,他说:「杀青了。」我后来才知道,他用原本分配给另一部短片的资金拍摄了这部剧情长片。然后,他用剩下的三天时间拍完了那部短片,是与《在异国》中的一位女演员合作完成的。情况大概就这样……我对成果非常满意。
《在异国》
傅东:2017年,你们再次合作拍摄了《克莱尔的相机》。
于佩尔:那一年,我和他各有一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展映。他的是《之后》,我的是保罗·范霍文执导的《她》。他提议趁此机会六天内在戛纳拍摄一部电影,我立即同意了。我提前抵达戛纳,履行与哈内克的电影《快乐结局》(2017)相关的工作,而他为我租了一间位于戛纳、远离海滨大道的小公寓。
就这样,与他不久前结识的演员金敏喜(我和她相处得非常融洽)一起,我们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拍摄了一部电影,几乎没有察觉到时间的流逝。这有点像一场梦。这次完全没有剧本。他真正是在拍摄过程中即兴创作了《克莱尔的相机》。
《克莱尔的相机》
傅东:然后就是这部新作……
于佩尔:2023年2月,法国电影资料馆举办了他的作品回顾展。当时我不在巴黎——我正在其他省拍戏——但我还是回去跟他见了面。我们聊了很多,两个小时后,他说:「一起再拍一部电影该多好啊。」我立刻答应了。他回到了韩国,四月初,他寄给我一张6月11日出发的机票。我出发时对这部电影一无所知,但充满信心和喜悦。
《旅行者的需求》
傅东:他没有给出任何提示吗?
于佩尔:除了关于服装的想法。他坚持一定要穿连衣裙,而且要短款的。我给他发了照片,但都没有合适的。出发前一天,收拾好行李后,我逛了逛家附近的商店,在一家我平时不会进去的店里,我看到橱窗里有一件连衣裙。我试穿了那件裙子,给他发了照片。他的回复是:「完美!」售货员说:「我们还有一些开衫可以搭配这件裙子,」她拿出一件绿色的开衫,后来这件开衫在电影中频繁出现。我又给他发了照片。这正是他想要的。于是,我出发了。
傅东:但在那时,你对这个角色还是一无所知?
于佩尔:完全空白!第一天晚上,他把所有演员和整个剧组都召集到他家(除了现在还要负责制作的金敏喜,其实只有两个人——一个负责声音的工作人员,以及一个助理),还有我的翻译。那是一次非常温馨的聚会,但我仍然不知道更多信息。然后他给了我第一天的拍摄剧本,也就是第二天要拍的内容。那时我才意识到要背的台词量巨大。
傅东:一切都写在剧本上了?这部电影感觉像是拍摄过程中即兴创作的。
于佩尔:一切都写好了,非常精准。而且非常严谨,投入了大量心力。没有任何即兴发挥,然而在他提供的严格框架内,却有着巨大的自由度。一切既轻盈又精巧。这非常令人着迷。个人而言,我愿意和他再拍十部这样的电影。
傅东:他一场戏会拍很多条吗?
于佩尔:是的,很多。他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指示,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,而是让我们自己去探索,与他一起探索。这就是自由所在。他在同一场景的不同镜头之间不会做出重大改动;他要寻找一种氛围、一种色彩、一种节奏,而我们,作为演员,也与他一同探索。这个过程也正是让我们能够将那些场景变得有趣的时刻,尽管其中并没有什么天然喜剧性的事情发生。
傅东:布景、室内空间似乎也充满深意……
于佩尔:这其实是部分演员们真实居住的公寓!三个主要室内取景地正是李慧英(饰演我的第二位学生)和河成国(饰演和我待在一起的年轻男子)的真实住所。第一个公寓实际上是权海骁(饰演李慧英的丈夫)的住所。这都源于始终追求最简单、最经济的制作原则,而且洪常秀将此视为优势而非局限。
傅东:这一点似乎同样适用于剧组。
于佩尔:是的,现在和他一起工作的只有三个人。他可以用一台有时甚至难以发现的微型相机,在没有摄影指导和任何打光设备的情况下,拍摄出美丽的画面。
傅东:他总是能充分利用自然光,但这必然让他受制于天气。
于佩尔:确实如此。事实上,有一天突然下雨了,我们没能拍摄。从制作角度来看,这简直是个奢侈的决定,但他那天就是不想要那种光线。他说:「今天不拍了,我们等到明天再说。」而我们总共只有十三天的拍摄时间!
傅东:在这部电影中,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,很多事情都是通过你的语调来传达的,尤其是当你的语调在英语和法语之间切换,以及有时在酒精的影响下变得含糊时。
于佩尔:确实。这并非完全自主可控的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化学反应,也受到身处韩国的影响,一个与我的文化相去甚远的国度。我注意到,尽管并非有意为之,但我的说话方式中始终带着一种惊奇或质疑的语气,这体现在我经常说出「哦!真的吗?」之类的话。这种语气让我与周围环境保持了一种温柔的距离,即使有时其中夹杂着悲伤、担忧或幽默……这既符合角色设定,也反映了我的个人处境。
傅东:你的角色的另一个鲜明特点,或者说你表演的另一个鲜明特点,就是你的走路方式。
于佩尔:没错!这对我很重要。我总是会考虑这个问题;对于每一个角色,我都会研究自己的走路方式。在这部电影中,我穿着在马德里买的那些带跟的凉鞋,它们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戏剧性的元素。
傅东:你的角色喝了很多韩国米酒,也就是马格利酒,这种酒在洪常秀的电影中经常出现。你喜欢喝吗?
于佩尔:喜欢。我在拍戏时喝的是真酒。我从来不喜欢烈酒,但我真的很喜欢马格利酒,它为场景增添了活力。但拍摄时我从未喝醉过。
傅东:在拍摄过程中,是否会有一些情况需要你提出建议,例如在说法语的场景中,当你的角色为学生制作单词卡片时?
于佩尔:是的,但我得到了我的翻译的很大帮助,他是一位文学翻译家,法语说得非常好。我们一起精确地调整了那些非常具体的词汇,这些词汇与所有角色所说的英语不同,尽管这都不是我们的母语。然后我在卡片上手写了那些小段文字,我喜欢洪常秀完整地拍摄这些时刻,给这些小段文字留出时间。
傅东:绿色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,似乎从你的角色所穿的开衫毛衣那独特的绿色开始展开……
于佩尔:是的,这种绿色确实为影片增添了一抹神奇的色彩;当然,这主要是因为洪常秀拍摄我的方式,以及他拍摄色彩的方式,才产生了这种效果。在其他情况下,可能没人会注意到这一点。从绿色开衫开始,各种变体出现了,比如笔上的绿色胶带,或者我所处的绿色涂装的阳台。这些都是在洪常秀的拍摄中经常出现的快乐意外,因为他的拍摄方式为它们留出了空间。
傅东:他在剪辑时是否会删减某些场景,去除某些已经拍摄的素材?
于佩尔:这种情况发生在影片结尾处的一个很长的镜头,我与一位在街上遇到的年轻女子对话,她为我翻译了一首诗。顺便提一下,这位年轻女子由我的翻译饰演。这个场景包含了大量解释性内容。她向我讲述了她的生活,而我也向她介绍了自己的背景以及为何会来到首尔。我们拍了很多次,但最终他剪掉了整个片段。这让电影更加神秘,更加暧昧。我认为他完全正确。
傅东:相较于与洪常秀的合作,你是否曾与其他导演有过类似的拍摄经历?
于佩尔:这很难说……我唯一能想到的比较对象可能是让-吕克·戈达尔。不仅因为没有预先写好的剧本,还因为他传递信号的方式,往往是间接的、暗示性的,并且在不经意间构建起一个参考网络:地点、颜色、音乐、片段等等,这些元素有助于我接近他的创作意图,即使他自己尚未完全明确。
这也通过行为方式、特定类型的幽默感得以体现,从而形成我所称的「表演代码」。它从未被明确阐述,恰恰相反,但它微妙地引导着演员在镜头前应如何表现,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。
傅东:目前,你每晚都在舞台上演出由罗密欧·卡斯特卢奇执导的《贝蕾妮丝》。你在戏剧和电影领域都非常活跃;你是否将它们视为独立的实践,甚至是独立的世界,还是作为同一门相通的技艺:表演?
于佩尔:它们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截然不同,然而,它们在某个点上相交。那个点,或者说那个时刻,是我一直在寻找的,那就是我不再觉得自己在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。这种状态在戏剧中更难达到,因为戏剧更加形式化,台词往往不似日常对话,舞台空间也非常固化,而电影则常常呈现出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情境。但在两种情况下,都有可能超越形式结构达到那种状态。而这些结构在电影和戏剧中各不相同,且因作品而异。
在两者中,甚至可以通过高度风格化、非自然主义的手段达到这种状态。要达到这种状态,有时会感觉像是在与文本进行一场真正的身体搏斗。这并非记忆的问题,而是通过文字进入另一个世界,这些文字可能出自莎士比亚或拉辛之手,也可能出自某位导演当天早晨的创作。你必须找到「活生生的切入点」。